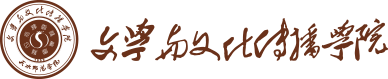编者按:2025年《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第六期刊发了我校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汪聚应的文章《先秦两汉谣谚与咏侠诗之滥觞》。文章已收录于知网。全文如下:
先秦两汉时期崇尚任侠,养士与游侠活动盛行。除正史文献外,民间歌谣时谚与史相依,广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游侠活动的生动内容。这些谣谚从社会生活史的视角,保存、补充或拓展了正史的相关内容,提供了当时任侠风尚和游侠生活的真实图景,积累了古代咏侠诗产生所必要的文学素材和基本的审美要素。作为我国古代咏侠诗的直接源头,先秦两汉谣谚在咏侠诗的基本主题、文学形象、人格精神以及诗体和艺术形式等方面哺育启迪了后世文人咏侠诗的创作,是中国古代咏侠诗从民间歌谣到成熟的文人诗创作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源发和承继关系十分清晰,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从古代任侠风气和咏侠诗的创作发展历程来看,古代咏侠诗的创作生发所关涉的社会文化层面非常丰富。从历史积淀看,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侠文化的实录阶段,先秦时的养士之风与侠义实践,两汉时期游侠刺客惊天动地的任侠活动,以及《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史书对当时游侠活动的历史记载,确立了侠义传统的基本道德观念和侠文化的要素基质,深刻影响了后世侠的现实行为及其人格精神。
从咏侠诗发展史的角度看,先秦两汉崇尚任侠,养士与游侠活动盛行。民间歌谣时谚与史相依,广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任侠风尚和游侠活动的生动内容,是咏侠诗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些与任侠风尚有关的歌谣时谚,在口耳相传中从侠的文化基质、文学素材和审美元素等方面,以独特的现实背景、饱满的文学形象、鲜明的审美指向,为咏侠诗的创作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主题与题材、审美指向和价值观念。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作为咏侠诗的直接源头,它根植于现实生活,在反映时代任侠风气和游侠生活方面鲜明生动,自可成为正史佐证和研究游侠社会生活史的重要资料,足以补充拓展游侠史的现实生动性和丰富性,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在侠文化研究中,先秦两汉的咏侠歌谣、时谚,大多散见于史籍中,很少受到关注和挖掘整理研究,但这些“散见在史籍中极少数的片谣只歌”实为“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其作为历史资料的史学价值、民俗价值和文学价值不容忽视。本文试图通过对先秦两汉咏侠歌谣时谚的广泛搜集整理和整体审视,进一步挖掘古代咏侠诗创作的现实基础和文学渊源,勾勒出我国先秦两汉咏侠谣谚的史料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从游侠发展史看,先秦两汉是游侠现实存在的重要历史时期,任侠与养士之风炽盛,游侠阶层随之不断壮大,反映游侠生活的歌谣时谚开始繁荣。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先秦两汉是中国古代咏侠诗的滥觞期,作为咏侠主题确立前期的雏型作品,形式多为表现简单直白的歌谣与时谚,文体特征尚未成熟,且多与史传、辞赋等其他文学形式相混。如班固《西都赋》《东都赋》,张衡《西京赋》都在描写都市生活,展现了侠者风采。甚至有学者认为“咏侠诗潮滥觞于东汉大赋。”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先秦两汉游侠风貌和游侠存在的真实状况,展现了游侠丰富的社会生活、复杂的社会关系、鲜明的任侠精神,积累了咏侠诗创作生发的现实素材、文学形象和文化精神,成为古代咏侠诗的直接源头。
就先秦两汉咏侠歌谣时谚来看,一是数量较少,篇幅短小。据统计,在420余首两汉谣谚中,有117首生活经验、哲理类谣谚,126首人物品评类谣谚,49首谶谣以及83首政治评判类,13首神仙信仰类,21首地理风貌和风土民情类,10首志怪类,13首农家谣谚类谣谚。这样看来,两汉谣谚数量不少。笔者依据《史记》《列女传》《古谣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统计,先秦咏侠歌谣时谚包括《弹铗歌》《河激歌》《徐人歌》《荆轲歌》《渔父歌》《鲁孝义保颂》《鲁义姑姊颂》《齐义继母颂》《魏节乳母颂》《梁节姑姊颂》《合阳友娣颂》《京师节女颂》《伍子胥歌》等共计13首。依据《史记》《汉书》《古谣谚》《乐府诗集》《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统计,两汉咏侠歌谣时谚包括《颍川儿歌》《时人为郑庄谚》《长安为尹赏歌》《长安百姓为王氏五侯歌》《闾里为楼护歌》《刘圣公宾客醉歌》《曹邱生引楚人谚》《关东为宁成号》《太史公引鄙语论游侠》《太史公又引谚语论游侠》《诸儒为朱云语》《长安为谷永楼护号》《时人为戴遵语》《临淮吏人为朱晖歌》《并州歌》《顺阳吏民为刘陶歌》《时人为杨阿若号》《蜀中为费贻歌》《益都民为王忳谣》共计19首。在先秦两汉广阔的历史时期,这三十多首咏侠歌谣虽然数量少,但足以展现当时游侠活动的生动现实和丰富内容。
二是这些歌谣所咏人与事都与侠义有关,为游侠精神灌注了极其生动的人格魅力。在先秦两汉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行游于列国之间的战国游侠、秦汉游侠少年,以及汉代侠的豪强化,侠的现实存在、历史记载与慷慨歌谣相为表里,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游侠活动、重义轻生的任侠精神,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文化影响。从先秦两汉史家,以及歌谣时谚反映的“侠”与“义”的内容来看,尽管游侠行为时有与社会规范的偏离,但侠客之义、复仇意识、牺牲精神足以反映出游侠的血性与精神。
从当时史家的认识评价看,中国侠文化史上,韩非首先以法家立场和正统社会规范来评判游侠,其“侠以武犯禁”,表明当时作为“私剑”的群侠,其“以武犯禁”的行为自然“不轨于正义”。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立《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并在对游侠行为和人格精神的评价中,首次将“义”作为重要的标准。虽然这种以“义”为核心的侠义观念,主要指向“侠客之义”,并非正统观念和伦理价值意义上的“正义”,但它精准概括了游侠的人格精神和价值观念。基于此,司马迁认为先秦刺客之侠“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赞扬西汉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另外,对待游侠这个群体,司马迁也不是不加区分地一概而论,而是以“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及其与之相比较的“有土卿相之富”“朋党宗强”和侠的末流“暴豪之徒”等相区别对待。肯定布衣闾巷之侠仁义贤豪的处事行为和贤良豪爽的人格特征,赞扬他们贤能于世的艰难与不易。
与韩非、司马迁相比,班固对游侠的评价,兼顾了个人与国家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游侠者个人精神层面肯定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另一方面,又从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层面批评养士任侠行为导致了“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东汉荀悦更是以“伤道害德,败法惑世”评判游侠,认为游侠与“三游”之“游说”“游行”一样,是“德之贼”。
司马迁、班固一方面肯定秦汉游侠的“侠客之义”,但又清醒理性地指出其“不轨于正义”的一面。这是从游侠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方面来认识评价游侠的。其个性张扬、追求享乐甚至不义等行为特征,确实是侠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但这些任侠行为在历代任侠风气中通过“游侠少年”这个特殊的群体为文人对侠的义化改造提供了前提,也为在诗歌、小说中塑造血肉丰满、富有个性的游侠形象奠定了基础。
就表现内容看,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反映了作为实录阶段游侠的热爱自由、张扬血性和侠义观念,以及超越世俗的荣名与气节,展现了侠义之士冀知报恩、重诺轻生、借躯报仇的任侠精神,言信行果、急难解困的侠客之义,温良泛爱、轻财好施的人格风范。
相对而言,先秦咏侠谣谚反映的侠者行为更为血性张扬和富有牺牲精神。有的表现侠义之士借躯报仇的牺牲精神。如《荆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表现荆轲为燕太子刺杀秦王义无反顾的侠义精神。这首歌见《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被称为“游侠诗的鼻祖”。从咏侠诗的发展来看,《荆轲歌》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时空和更远的文学史长河深刻地影响了古代咏侠诗的主题类型生成与题材生长,从一个侠者的悲壮生发为文人对功业价值追求的认同,从一个历史时空走向诗歌、小说、戏剧等广阔文学殿堂。有的表现侠义之士冀知重诺的人格风范。如《徐人歌》:“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带丘墓。”这首歌谣在刘向《新序》卷七中列为《节士篇》,亦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写的是延陵季子与徐君重诺感知己侠义事。《新序》卷七曰:
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徐君观剑,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然其心已许之矣。致使于晋,顾反,则徐君死于楚,于是脱剑致之嗣君。从者止之曰:“此吴国之宝,非所以赠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赠之也,先日吾来,徐君观吾剑,不言而其色欲之,吾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虽然,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伪心,廉者不为也。”遂脱剑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无命,孤不敢受剑。”于是季子以剑带徐君墓树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徐人歌》赞扬的是侠者的知己情结。冀知报恩在先秦两汉时期的侠意识中异常浓烈,其内涵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得到了丰富和提升,一跃而为“士为知己者死”的明主情结与恩报意识,成为先秦游侠重要的侠意识内容和独具时代特色的侠义人格精神,反映了深厚的现实内容和鲜明的时代文化心理。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出当时任侠之士的执着和牺牲精神、追求功名的价值理想和张扬个性自由的人生情趣,为我们认识当时侠义之士复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有的表现了民间侠义之士重义轻生的侠义精神。如《渔父歌》《伍子胥歌》等。《渔父歌》云:
日月昭昭乎寝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寝急兮将奈何?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
伍子胥逃楚事见《吴越春秋》卷三。这首《渔父歌》描写的是渔父渡伍子胥逃难及为绝其信息而投江自沉事,赞扬的是民间侠义之士扶危济困、重诺轻生的侠义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女性中亦多侠义之士,并被诉诸歌咏。且从她们的行为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侠义精神的普遍认可和自觉践行。如《伍子胥歌》中的濑女,《河激歌》中的女娟及《鲁孝义保颂》《鲁义姑姊颂》《齐义继母颂》《魏节乳母颂》《梁节姑姊颂》《合阳友娣颂》《京师节女颂》等中的侠义女性等。这些歌谣,表现着侠义女性的轻生守信、舍己为人的侠义精神和以死效义的气节。
濑女事见《伍子胥歌》,其云:“俟罪斯国志愿得兮,庶此太康皆为力兮。”此歌谣歌咏伍员奔吴,濑溪女子为之济食,守密而自投濑溪的侠义之事。《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一云:“伍员奔吴,过溧阳濑溪,见一女击漂于水中,旁有壶浆,乃就乞饮。饮毕,谓女子曰:‘掩夫人壶口。’女子知其意,自投濑溪而死。”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引《吴越春秋》曰:“伍子胥伐楚还,过溧阳濑水之上,长叹息曰:‘吾尝饥,于此乞食,而杀一妇人。将欲报之百金,不知其家,遂投金濑水之中而去。’”
《河激歌》歌咏河津吏引醉失渡,其女娟敢“以微躯易父之死”的侠义事。另如《鲁孝义保颂》歌咏伯御作乱,鲁孝公称之保母以自子代公子称而死侠义事;《鲁义姑姊颂》歌咏齐攻鲁时,鲁野之妇人义姑姊弃自子而存兄之子侠义事;《齐义继母颂》歌咏齐义继母信而好义、洁而有让侠义事;《魏节乳母颂》歌咏秦攻魏时,魏节乳母守忠死义侠烈事,等等。
汉代游侠颇重侠客之义,表现出重诺轻生、言信行果、急难救困等方面的高尚侠品,故汉代民间咏侠歌谣,有对侠义之士的赞怀:如《顺阳吏民为刘陶歌》“邑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太史公引鄙语论游侠》“何知仁义,已向其利者为有德”;《曹邱生引楚人谚》“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时人为戴遵语》“关东大豪、戴子高”。这其中赞誉西汉末年侠义之士朱晖的《临淮吏人为朱晖歌》,是此类歌谣最具褒奖和感情倾向的。其云:
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人怀其惠。
朱晖是西汉末年一位有名的官侠,早孤,有气决。史书记载他有气勇,好节慨,重然诺,专趋人之急。此歌寥寥四句,通过临淮地方官吏和百姓对朱晖的情感态度,表现了百姓对朱晖这样一位具有侠义心肠官员的赞美。它表现出汉代游侠存在亦官亦侠的特点。
汉代民间咏侠歌谣,有的歌咏游侠借躯报仇解怨等行为。如《时人为杨阿若号》:
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
杨阿若事见鱼豢《魏略·勇侠传》,载其“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但这首赞扬他少年任侠行为的歌谣当为汉代,且杨阿若在汉末建安时期亦有为徐揖报仇之事。
汉代民间咏侠歌谣,也有对“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等极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豪侠的反映。如《长安为谷永楼护号》“谷子云笔札,楼君卿唇舌”;《闾里为楼护歌》“五侯治丧楼君卿”。
在汉代民间咏侠歌谣中,表现游侠的集团化和豪暴侵凌等行为的一些作品,是对汉代游侠豪强化、权贵化新现象的反映。两汉养士之风很盛,当时一些地方出现了任侠集团,多是豪强等个别侠魁纠合侠少、宗亲等势力而成,称霸一方,或与官员相勾结,欺压百姓。如《颍川儿歌》云“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长安百姓为王氏五侯歌》“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其中《颍川儿歌》反映的是对颍川灌氏豪侠集团威势的不满以及对其灭族的快意。这是汉代游侠豪强化、权贵化的反映。《汉书·灌夫传》记载道:
夫不好文学,喜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
灌夫喜任侠,通豪杰,蓄宾客,灌氏豪侠集团威势嚣张,颍川百姓深受其害,故以此歌谣流传泄愤。
值得注意的是,两汉游侠炽盛无忌,连党结群,“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威重于守”“二千石莫能制”。他们豪暴侵凌,作威作福,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统治者便任用酷吏进行残酷镇压。故对酷吏整治游侠的歌咏也成为汉代民间咏侠歌谣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关东为宁成号》《长安中为尹赏歌》等。
《关东为宁成号》以“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表达了对酷吏宁成的痛恨和恐惧。《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宁成“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其为官治民“如狼牧羊”,狠毒阴险。汉代这类咏侠谣谚中,最突出、最具影响的是《长安中为尹赏歌》:
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
这是一曲为游侠少年唱出的悲凉挽歌,反映的是酷吏尹赏对长安游侠进行残酷屠杀的场景。以五言四句的形式,抒发了人们对游侠少年的痛惜之情,对酷吏以恶为治的不满以及对慕侠少年的警诫。据《汉书》卷九○《酷吏传》记载,尹赏于长安狱中修建“虎穴”,并通过户曹掾吏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等,检举长安轻薄少年恶子等数百人,分行收捕,见十置一,以百人为辈,入虎穴中,并以大石覆盖。“数日一发视,皆相枕藉死,便舆出,瘗寺门桓东,楬著其姓名,百日后,乃令死者家各自发取其尸。亲属号哭,道路皆歔欷。”长安中因有此歌。
从中国古代咏侠诗史的角度看,先秦两汉咏侠歌谣时谚内容丰富、感情真挚,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先秦两汉游侠真实的生存状况,揭示了当时丰富生动的任侠活动,其中也包含着当时民间社会对游侠的爱憎褒贬之情。作为咏侠诗萌芽期的作品,它们还算不上真正成熟的咏侠诗,但其朴素真挚的风格对后世咏侠诗的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影响,对从起源与发展流变视角研究我国古代咏侠诗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其奠基开创作用不容忽视。
二、先秦两汉谣谚的文学史料价值与咏侠诗主题题材的孕育
先秦两汉谣谚,尤其是其中的咏侠谣谚,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也值得重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游侠风貌和生存状况,提供了真实生动的游侠生活史,拓展、丰富、补充了正史记载之不足。二是记载保留了一批个性特异的历史侠的生动形象。三是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游侠的社会评价,与游侠的历史评价相得益彰,成为侠的文化基质和文学形象的重要内涵。”
从先秦两汉咏侠歌谣时谚的文学史料性看,先秦两汉咏侠谣谚与正史相得益彰,反映了当时游侠的现实生活实景。其所咏游侠的生动形象、人格精神及其社会评价,奠定了中国侠的文化基质,促进了古代咏侠诗主题与题材的形成。其对后世文人咏侠诗主题与题材的孕育和促进作用体现在:一是先秦两汉咏侠谣谚歌咏的游侠行为及其任侠精神,提供了后世文人咏侠诗主题性创作素材;二是先秦两汉咏侠谣谚丰富生动的审美个性,提供了后世文人咏侠诗鲜明的侠义人物形象;三是先秦两汉咏侠谣谚独具特色的侠义文化内涵提供了后世文人咏侠诗极富审美价值的人格精神。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游侠风貌和真实景况,提供了真实生动的游侠生活史,为古代咏侠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从中国侠文化发展历史看,先秦两汉时期是任侠的活跃期,也是侠的历史存在最为原始真实的阶段。广阔的列国时空和崇尚任侠养士的现实环境,不但为滋养游侠的原始血性、侠义人格提供了土壤,而且为他们尽力展示特立独行的绝异自我提供了活动舞台和价值空间。从侠的演变所形成的历史侠、文学侠、文化侠等不同的文化类型看,从侠的文化载体发展所形成的实录阶段与文学虚构阶段所展现的侠的群像与个体人格精神看,先秦两汉作为实录阶段侠的真实活动时期,正是如《史记》《汉书》等史书实录与民间咏侠歌谣、时谚口头实录的共同作用,才使当时的任侠风尚和游侠活动得以相互补充,游侠有血有肉、神采丰满,更使这一时期对侠的记载能够做到文史合一、历史记载与现实生活交辉合璧、互为依据。这在中国侠文化发展史上是唯一的。而最富生活现实感的咏侠歌谣、时谚,无疑成了真实反映当时游侠风貌和存在状况的一部真实生动的游侠生活史。
从咏侠诗发展历史看,诗歌中咏侠主题与题材的确立,包括这类诗歌主题内容的生发都有一个逐渐积累和丰富的过程。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先秦两汉咏侠谣谚的先导作用和基础性作用、价值赋能性作用不可忽视。
首先,先秦两汉咏侠谣谚通过描写当时炽烈的游侠风气、通过歌咏任侠之士,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文学素材。我国诗歌发展史的经验表明,古代每一种诗歌体裁和题材最早都是在民间孕育,然后文人进行模仿创作,最后形成一种新的诗体或题材。而一种诗歌题材内容能否成为诗歌的主题类型,就要看它在诗歌发展长河中的持久性、稳定性,以及文人的审美情趣和大众的接受程度。游侠作为一种特别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任侠风气在古代作为普遍的社会思潮,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和大众的英雄崇拜心理。而中国古代文人由于自身的功业追求、理想人格向往,往往借侠张扬自我,抒发豪气干云的情怀,即所谓“豪气一洗儒生酸”“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使得文人对游侠情有独钟,不断对其进行“义化”改造和理想化、英雄化、文人化的艺术创造,最终使咏侠题材绵绵不绝,不断掀起一个个咏侠诗潮。而他们在咏侠诗创作中对历史传统非常看重,因此也非常看重流淌在古游侠身上的侠义品质和游侠情怀。这使先秦两汉咏侠谣谚所歌咏的侠义人物、任侠行为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人格精神成为沉淀在咏侠诗创作发展长河中稳定不变的主题,从而也为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形成咏侠主题类型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同时,先秦两汉咏侠谣谚记载保留了一批个性特异的游侠的生动形象,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游侠的社会评价,形成了侠的文化基质,为古代咏侠诗的创作提供了诗歌形象、思想内容和价值指引。
文化基质是指在某一特征性文化形成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稳定性的文化因素。从侠文化和侠文学的发展角度看,先秦两汉咏侠谣谚表现的任侠风气以及游侠行为,对中国咏侠诗文化基质的形成、侠义人格精神的确立和价值观念的形成都带来了广泛影响。
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侠文化的发轫期和侠文化基质形成的重要时期,深入挖掘和准确把握这些基质内涵,对研究侠文化和侠文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先秦两汉游侠的行为特征看,以“利他”为核心的“侠客之义”,作为行侠的准则和侠者的重要标识,在秦汉游侠的行为中已有普遍性和超异性的表现。这些特征性的要素,主要来自史家评价。如“士为知己者死”的明主情结与恩报意识;“立意较然,不欺其志”的人格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精神操守;“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的绝异之姿等,都是侠文化中积极的文化基质和具有核心价值的文化要素,虽然当时游侠的利他行为有正义的、非正义的,但“利他”确实是秦汉时期侠文化中一个特别的价值性特征,是中国侠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文化基质,也是先秦两汉咏侠谣谚极力赞赏的主要思想内容。它们通过咏侠谣谚成为诗歌中最初的古游侠形象具有的行为特征和侠义人格精神,成为古代咏侠诗基本的思想内容和审美追求。而游侠“不轨于正义”的消极一面作为侠文化的基质因素,有着张扬个性、追求享乐的世俗特征,为文人对侠的义化改造提供了前提,为诗歌中塑造血肉丰满、富有个性的游侠形象奠定了基础。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对游侠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评价总体持肯定态度,诸如知恩图报、不畏牺牲、重诺轻生、急难解困等侠义人格精神,尤其在世俗道义方面的评价,体现着与正史的一致性。这也是其史料价值的体现,为侠的文化基质和文学形象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内涵。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在展现游侠行为观念,咏赞游侠人格精神中,对中国侠文化基质的形成与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赋予了咏侠诗深厚的思想内容。从后世咏侠诗的创作内容看,一些基本的、稳定性的内容来自先秦两汉咏侠谣谚的积淀与影响。如“重信守诺”“损己助人”“不矜其能”“轻生重义”“冀知报恩”“借躯报仇”等富含侠气、侠情、侠节的侠义人格精神,以及一些特征性的主题内容,在历代歌咏古游侠的诗篇中几乎是相沿习用的。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通过描写当时炽烈的任侠风气,歌咏任侠之士,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一种基础性的文学创作素材。古代文人一方面借侠张扬自我,涵养豪气干云的气概,同时不断对其进行“义化”改造和理想化、英雄化的艺术创造,最终使咏侠题材成为绵绵不绝的咏侠诗潮,并使咏侠谣谚所歌咏的侠义行为及其人格精神,沉淀为咏侠诗创作中稳定不变的主题内涵,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咏侠主题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后世咏侠诗中侠义英雄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先秦两汉咏侠谣谚的哺育。尤其是先秦两汉咏侠谣谚中所歌咏的荆轲、季扎、伍子胥、渔夫、濑女、灌夫、楼护、戴遵、杨阿若、秦女休等古游侠,为后世文人咏侠诗的创作提供了侠义英雄形象和个性化素材。而以对荆轲、季扎与秦女休的歌咏数量尤多,见于历朝历代咏侠诗。不但唐人咏侠诗和后世咏侠诗中歌咏荆轲的诗篇多如牛毛,仅就咏侠诗初创时期的魏晋六朝,歌咏荆轲的诗篇计有王璨《诗》一首、阮瑀《咏史诗二首》之二、左思《咏史诗》八首之六、陶渊明《咏荆轲》一首、刘骏《咏史诗》一首、周弘直《赋得荆轲诗》一首、杨缙《赋得荆轲诗》一首共七篇。
从后世咏侠诗的题材内容看,咏侠诗自先秦两汉咏侠谣谚之滥觞,发展成为诗歌创作的主题类型和绵延不绝的咏侠诗潮,期间或因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在咏侠诗内容上虽有体现时代价值观念的不同,但一些基本的、稳定性的内容却来自先秦两汉咏侠谣谚的积淀和影响。如咏侠诗中描写歌咏侠者“诚信守诺”“重义轻生”“冀知报恩”“借躯报仇”等侠义人格精神,为后世咏侠诗主题内容的提升灌注了侠义人格精神。这些特征性的主题内容,在历代歌咏古游侠的诗篇中几乎是相沿习用的。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是中国古代咏侠诗从民间歌谣到成熟的文人诗创作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源发和承继关系十分清晰。它们积累了咏侠诗产生所必要的文学素材和基本的审美要素,不但在咏侠诗的基本主题与题材、游侠形象和人格精神等方面哺育启迪了后世文人咏侠诗的创作,而且在诗体和艺术形式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起到了奠基作用:一是创作题材方面主题性素材的提供;二是人物形象塑造上侠义形象的丰富与人格精神的灌注;三是以“侠客之义”和“冀知报恩”等侠义人格精神赋予古代咏侠诗鲜明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基础;四是孕育形成了后世文人咏侠诗最初的艺术体制、基本母题和诗歌体式以及清新自然的美学风格。与大多数文学形式的发展成熟规律一样,古代咏侠诗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先秦两汉民间歌谣时谚的哺育启迪。通过对后世咏侠诗的发展追溯,从先秦两汉民间咏侠歌谣到成熟的文人咏侠诗创作,期间的源发和承继关系十分清晰。可以说,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孕育了后世文人咏侠诗的创作和发展,是我国古代咏侠诗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从艺术表现方面看,先秦两汉咏侠谣谚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感情率真,爱憎分明,语言朴素凝练,琅琅上口,便于流传。其修辞手法的运用也很成熟,从多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游侠的生存状况以及人们的态度。它们不但为咏侠诗的创作提供了生动的题材,同时也在艺术表现上形成了咏侠诗最基本的审美特点。
先秦两汉咏侠歌谣在咏唱的内容和形式上,为中国古代咏侠诗的产生发展积累了基本的诗歌主题、游侠形象和人格精神。在先秦两汉咏侠歌谣中,后世文人咏侠诗常见的基本母题已见端倪,如《结客少年场行》《游侠篇》这些古代文人咏侠诗常用的题目,就是由汉代民间歌谣发展衍变而来的。另外如《少年行》《游侠曲》《侠客篇》《侠客行》《侠客》等诗题,也从民间咏侠歌谣发端,经过文人的修饰润色和加工使用,最后成为历代咏侠诗通用的诗题,其中的继承演变和创新发展关系清晰可见。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形成了古代咏侠诗最初的艺术体制。从咏侠诗艺术体制的形成和艺术手法的积累看,先秦两汉咏侠谣谚的先导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先秦两汉咏侠谣谚质朴自然的艺术风格,对后世咏侠诗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传导性作用。“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在为后世咏侠诗创作提供主题与题材的同时,也把清新、自然、质朴的艺术风格带入其中,为后世咏侠诗创作带来了本质性的风格特征,而自然质朴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咏侠诗基本的艺术风格。二是先秦两汉咏侠谣谚中,业已形成了文人咏侠诗的基本母题和艺术体制。先秦两汉时期,游侠不仅广泛存在于民间社会,而且成为民间文学口头诵唱的一个基本母题。它们是文人咏侠乐府诗的真正源头。此时的咏侠谣谚中,一些歌谣对形成乐府咏侠诗诗题和形式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汉代咏侠歌谣《长安为尹赏歌》《东门行》两个题目。《东门行》直接成为乐府咏侠诗题。《乐府解题》曰:“古词云:‘出东门,不顾归。入门怅欲悲。’言士有贫不安其居者,拔剑将去,妻子牵衣留之,愿共餔糜。不求富贵。且曰‘今时清,不可为非’也。若宋鲍照‘伤禽恶弦惊’,但伤离别而已。”而《结客少年场行》诗题及其体制,就是在《长安为尹赏歌》基础上形成的。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六“杂曲歌辞六”《结客少年场行》云:
《乐府解题》曰:“《结客少年场行》,言轻生重义,慷慨以立功名也。”《广题》曰:“汉长安少年杀吏,受财报仇,相与探丸为弹,探得赤丸斫武吏,探得黑丸杀文吏。尹赏为长安令,尽捕之。长安中为之歌曰:‘何处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复何葬。’按《结客少年场行》,言少年时结任侠之客,为游乐之场,终而无成,故作此曲也。”
《结客少年场行》本是对尹赏镇压游侠少年结客报仇解怨等行为的感叹。尹赏以残酷手段大肆屠杀游侠少年,长安百姓恐惧怨愤,而为之歌,后成为文人咏侠诗《结客少年场行》题目的来源。陈山《中国武侠史》中说:
像郭茂倩在上述题解中所引用的长安民歌这样一类作品,在当时的民间社会一定屡见不鲜。这类民歌的“古辞”虽然如《宋书·乐志》所说“亡失既多”,但从仅存的这首长安民歌以及后代文人诗的基本内容框架可以“概见其义”,即都是专门咏唱少年侠行及其遭遇的。可见武侠不仅广泛存在于民间社会,而且逐渐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口头诵唱的一个基本母题。这一现象的出现,至少在西汉中期已经开始,它们是文人咏侠乐府诗的真正源头。
后世文人以《结客少年场行》歌咏游侠时,又演化出如《少年行》《少年子》《少年乐》以及《长安少年行》《邯郸少年行》《渭城少年行》等诗题。而《游侠篇》这一诗题,同样源于民间咏侠歌谣,后生发为文人咏侠诗的常用题目。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七“杂曲歌辞七”《游侠篇》云:
《汉书·游侠传》曰:“战国时,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故后世称游侠者,以四豪为首焉。汉兴,有鲁人朱家及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里,皆以侠闻。其后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时万章在城西柳市,号曰城西万章。酒市有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也。”《魏志》曰:“杨阿若后名丰,字伯阳,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后世遂有《游侠曲》”。魏陈琳、晋张华,又有《博陵王宫侠曲》。
《游侠篇》与《游侠曲》相同,在此基础上又演化出《侠客篇》《侠客行》《侠客》等诗题。
三是先秦两汉咏侠谣谚中一些艺术手法为后世咏侠诗提供了艺术借鉴。先秦两汉咏侠谣谚中一些艺术手法如起兴、比喻、夸张等修辞和用事用典手法为后世咏侠诗提供了基本的艺术借鉴,也成为后世咏侠诗常用的艺术手法之一。同时,咏侠歌谣时谚在用事用典上也为后世咏侠诗提供了借鉴。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展现了游侠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侠义人格精神,对中国侠文化基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文学主题、题材和体裁以及文学形象等方面对中国侠文学产生、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使中国侠和侠文学的创造传承成为史家与文人共建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史家的记载评价与文人的描写歌咏相互作用,使侠既成为史家较早立传的一类历史人物和现实存在,又通过史家的法正之路、文人的义化之路,以及大众的英雄之路,使侠成为后世文人寄予理想追求的文学母题。先秦两汉咏侠谣谚歌咏游侠的绝异之姿和惊天地、泣鬼神的侠行及其人格精神,为咏侠诗和武侠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和审美形象,成为中国武侠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产生的重要内驱力,同时也为武侠小说塑造侠义英雄人格提供了范本,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作者简介:
汪聚应,男,1966年出生,甘肃秦安人,文学博士、二级教授,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省级教学名师、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拔尖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核心专家库专家。现为天水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天水师大学学术带头人、中国古代文学重点学科带头人;陕西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兼职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甘肃省古代文学学会、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天水师范学院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负责人,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天水师范大学学报》主编。
汪聚应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在《文学遗产》 《光明日报》等国家核心刊物发表论文五十多篇,在中华书局等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专著《唐代侠风与文学》《唐人豪侠小说集》《中国古代咏侠诗史》《历代代咏侠诗集》四部,主编获参编多部。其学术论著及其学术观点被多家刊物引用、转载或加以介绍。并多次获得省部级奖励。学术成果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获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两次。获甘肃省教学成果省级特等奖一次、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持省级以上科研项目八项,其中“唐代侠风与文学”“中国古代咏侠诗研究”“唐人豪侠小说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